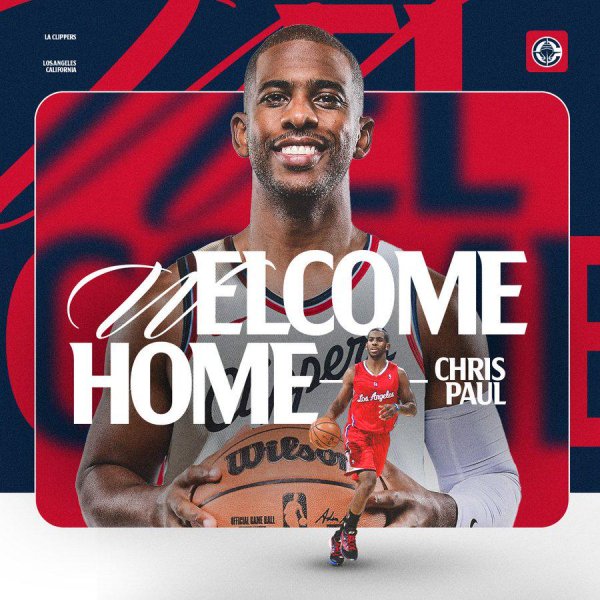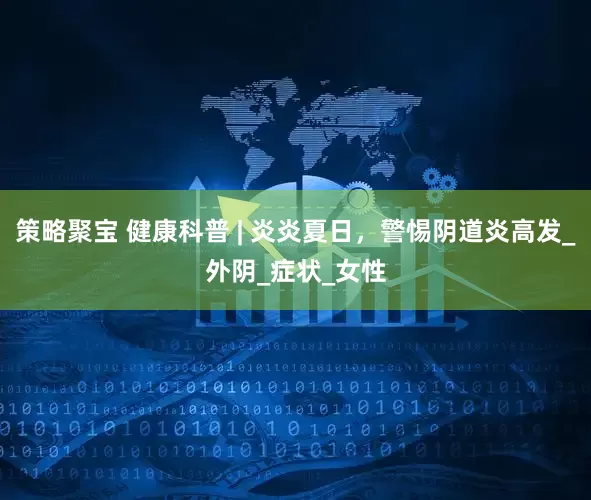导读:“明明是响应村里号召建设自己的房屋,并且也取得了用地许可证,为何刚建不久镇政府就将我们的房子强拆?”河南省Z市Y镇的陈先生手握两份截然相反的法律文书,陷入巨大的困惑。一份是法院确认镇政府强拆其六层住宅违法的生效判决;另一份竟是强拆两年后收到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金港赢配资,声称要“没收二层以上违建并拆除”——而该房屋早已化为瓦砾。
这场荒诞的法律博弈,揭开了征地拆迁中“以拆违促拆迁”的典型套路:当强拆被法院认定违法后,行政机关试图以事后处罚将既成事实“合法化” 。
1、废墟上的“补刀”:迟来处罚书背后的博弈逻辑
陈先生的遭遇始于十多年前。当时Y镇村委会鼓励村民自建房屋,他在获批地块取得用地许可证后,建成一栋六层住宅。房屋竣工不久,当地启动地铁建设项目,整片新建住宅区突遭征收。蹊跷的是:未见任何征收公告,村民对补偿标准、征收范围毫不知情;未签补偿协议,镇政府直接组织人员强制拆除房屋。
面对权益被践踏,陈先生委托律师提起行政诉讼。法院一二审均确认镇政府强拆行为违法,理由是“未履行征收法定程序,剥夺当事人申辩权”。
正当陈先生依据生效判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,一纸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期而至:“没收二层以上全部违法建设的房屋并予以拆除”——落款日期为2021年10月28日,距实际强拆已逾两年。
这份文书漏洞百出:无房屋具体地址、无面积数据、无公章、文号错误。更荒诞的是,其处罚对象竟是早已不存在的建筑。镇政府显然在赔偿诉讼启动后,试图以“补程序”掩盖违法本质。
2、以拆违促拆迁:征收方惯用的“法律武器化”
陈先生遭遇的二次伤害并非孤例金港赢配资。此类操作本质是将拆违程序异化为拆迁工具:
历史遗留问题被刻意“违法化”:农村房屋因管理粗放普遍存在手续不全问题,这本是行政机关长期监管缺位所致。但一旦涉及拆迁,这些房屋便被贴上“违建”标签。如河南高院在(2017)豫行终2450号判决中尖锐指出:“执法目的不是为了土地管理,而是为了避开法定征收程序,属于滥用职权” 。
拆违程序沦为快速拆迁通道:
合法征收需履行评估、协商、补偿等复杂程序,而拆违程序相对简易:乡镇政府直接认定违建(无需司法审查);下达限期拆除决定;快速实施强拆。
这种“捷径”使拆违成为规避《征收条例》的利器。河北唐山某工业镇在2019年即以拆违名义强拆数十家乡镇企业,后被法院认定“混淆行政强制与规划管理主体资格”。
事后“补刀”锁定赔偿额度:当强拆被法院判定违法后,行政机关常紧急启动违建认定程序。其核心目的正如陈先生案所示:将房屋定性为违建,大幅压缩后续赔偿金额。拆迁律师揭露:“若真属违建,拆迁方何必威逼签协议?实则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恐吓百姓”。
3、法律反击:戳穿程序把戏的三重逻辑
陈先生的拆迁律师针对《处罚决定书》发起精准法律反击,直指其本质违法:
实体消亡:处罚对象已灭失金港赢配资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条明确定义处罚对象是“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”。当房屋已被强拆,所谓“没收房屋”失去实施基础。福建福州类似案件中,法院强调:“对已拆除建筑再行处罚属程序空转,无实际规制对象”。
程序倒置:强拆在前认定在后
合法拆违必须严格遵循《行政强制法》流程:调查→告知→听证→决定→催告→强拆8。陈先生案中:强拆发生于2019年;违建认定却在2021年作出。程序严重颠倒,如同“先开枪后画靶”。
目的违法:规避国家赔偿
镇政府收到行政赔偿诉讼通知后突击制作处罚书,暴露出以处罚替代赔偿的意图。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判例中申明:“违法强拆后的赔偿不得低于补偿标准,且需弥补全部附属损失”。
复议机关最终采纳律师意见,以“事实不清、程序违法”为由撤销处罚决定。
4、维权启示:破解“拆违陷阱”的关键防线
陈先生的拉锯战揭示出征地维权中的核心防线:
锁定强拆程序合法性无论房屋性质如何,强拆均须遵守《行政强制法》第44条铁律:复议诉讼期内严禁强拆。河南郑州于泰和案中,乡政府未履行催告、申辩程序即强拆,法院直接确认违法。
追溯历史建设背景:
对因政策原因形成的“手续瑕疵房”,需挖掘历史正当性:90年代乡镇企业用地(如河北唐山案);村委会指定宅基地(如郑州王大勇案);政府许可的经营场所(北京玻璃厂案。
这些情形下,行政机关的先前允诺构成信赖保护基础。
警惕事后“法律补丁”:收到强拆后处罚文书时立即核查:文书记载与房屋现状是否矛盾;作出时间与强拆的时间差;是否针对已生效赔偿诉讼。如福建程某明案所示,对程序倒置的处罚书坚决提起撤销之诉。
尾声:废墟上的法律不会沉睡
陈先生案终以复议撤销处罚决定告捷,但博弈远未终止。镇政府强拆被判定违法、补刀式处罚被撤销后,行政赔偿诉讼成为最终战场。此案暴露出部分基层政府的操作逻辑:当强拆被法律狙击,便制造“程序回溯”以重夺主动权。
在河南高院判例中被定性的“不拆不查,一拆就查”的滥用职权行为,其危害远超个案补偿。它侵蚀公众对行政程序的信任,更将法律当作可任意拆卸的工具箱。
法律从不承认“过期”的权力,正如它永不宣告“过期”的权利。当陈先生们站在家园废墟上手握胜诉判决时,我们仍需清醒:阻止权力对程序的操弄,需要法庭内外的持续角力——因为当权力失去程序约束,法律便成为一纸空文。
五五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